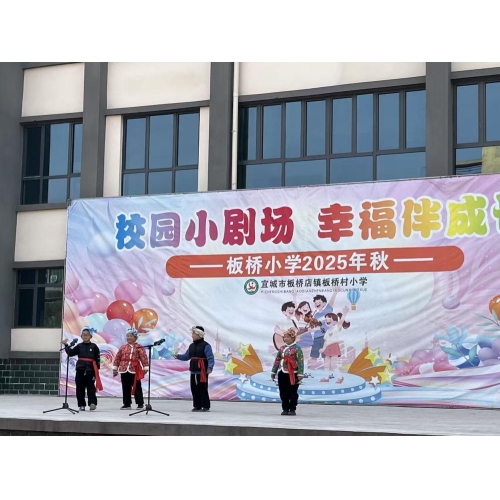当屏幕的光亮起时——冯 姣
周一早上七点,我们班的小何又一次没有出现在教室里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二次了。我打开他的作业,发现上周五的家庭作业只字未动。翻到前面几页,能清楚地看到作业质量逐日下降——从工整到潦草,从完整到空白,就像一部加速播放的植物枯萎纪录片。
我拨通了小何父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疲惫而暴躁的声音:“老师,这孩子我管不了了!昨晚又偷玩手机,凌晨三点才睡,现在还在睡觉!”我能听到背景音里小何父亲压抑不住的怒气,以及隐约传来的、孩子的啜泣声。
小何曾经是我们班的“开心果”。低年级时,我们陪他一起过生日,一起用餐,一起无话不谈,成绩稳定在中等。转变始于去年冬天。他迷上了网络游戏。
第一次察觉到问题是在一个周三的午后。数学课上,小何睡着了,头几乎要磕到桌角。我轻轻拍醒他,发现他眼睛布满血丝。“昨晚没睡好?”他含糊地点点头。那天下午的美术课,他画了一幅画:一个孩子坐在电脑前,窗外是漆黑的夜空,房间的角落里,一个人形的影子背对着他。
“老师,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在小何又一次缺课后,我决定去他家看看。开门的小何父亲双眼深陷,语气中充满了无力感:“我试过打,试过骂,试过把手机砸了,他把我的手机偷拿走,跑到山上躲起来玩一天都不回家,还耽误了我的工作。昨晚我们大吵一架,他摔门出去了...”在他们家后面的玉米地里,我找到了小何。九岁的男孩蜷缩着,校服皱巴巴的,眼睛盯着地面。
“小何,老师不是来批评你的。”我坐到他身边,递给他一个还温热的包子,“先吃点东西。”他迟疑地接过,小口吃着。长时间的沉默后,他忽然开口:“老师,你知道‘和平精英’吗?”
我摇摇头。“那是个需要队友配合的游戏。”他没有看我,自顾自地说,“我爸从来不跟我一起玩。他只会说‘别玩了’。”“那你为什么喜欢玩游戏呢?”“因为...”他停顿了很久,“游戏里的人会听我说话。赢了,他们会说‘干得漂亮’;输了,他们会说‘下次再来’。”他说得很轻,几乎被风吹散。
那天,我没有直接带小何回学校,而是陪他在河堤走了一圈。“小何,你看那棵树。”我指向一棵叶子发黄的银杏,“知道为什么它的叶子黄得比其他树早吗?”他摇摇头。“因为它根系附近的土壤太硬,吸收不到足够养分,也没有人给它修剪病枝。”我蹲下来,与他平视,“你现在就像这棵树。游戏不是问题,问题是除了游戏,你找不到其他获取‘养分’的方式。”他似懂非懂地看着我。“这样吧,我们做个实验。”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,画了一个圆圈,“这是你的一天24小时。我们来分配一下,看看哪些时间是必须的,哪些是可以选择的。”我们一起计算:睡觉需要9小时(我强调这个年龄需要充足睡眠),上学7小时,吃饭洗漱2小时,作业和复习2小时。“你看,已经20小时了。剩下4小时,你可以自由支配。如果全部用来打游戏,会怎么样?”“眼睛会疼,脖子会酸,第二天上课没精神。”他小声说。“如果我们把这4小时重新分配呢?比如1.5小时游戏,1小时运动,0.5小时和爸爸聊天,1小时做点别的——看书、画画,或者就是发呆?” 他低头想了想:“爸爸不会跟我聊天的。”“也许,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学会。”
接下来的两周,我实施了一个分步计划。第一步,我把小何的座位调到了第一排,并安排班级里最自律的班长做他的同桌。课间,我邀请他帮我整理作业本,创造自然交谈的机会。一次,他小声告诉我:“老师,我昨晚只玩了1小时游戏。”“感觉怎么样?”“有点不习惯,但早上起床不那么累了。”第二步,我与小何父亲进行了三次深度沟通。第一次,我请他停止打骂,分享了自己青春期时与父母的冲突。第二次,我带来了班级其他单亲家庭的成功教育案例。第三次,我给了他具体的建议:每周至少三次,每次15分钟,放下手机,专心听孩子说话——说什么都可以。“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。”小何父亲为难地说。“就从问他‘今天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’开始。”第三步,我在班级发起了“健康生活周”活动,记录每天的睡眠时间、运动时间和屏幕时间。小何被选为小组记录员,这给了他积极的正向压力。
变化是缓慢但可见的。小何的黑眼圈慢慢变淡,作业本上的字重新变得工整。一个周四的早晨,他主动告诉我:“老师,我和爸爸昨晚一起做了蛋炒饭。”“游戏呢?”“我们约好了,周末可以玩两小时,平时不玩。”他顿了顿,“其实我发现,不打游戏的时候,时间过得挺慢的,可以做很多事。”
教室窗外,那棵曾经过早枯黄的树,在园丁的精心养护下,今年秋天叶子金黄的时间,与周围的树同步了。而小何眼睛里的光,终于不再只是屏幕的反射。